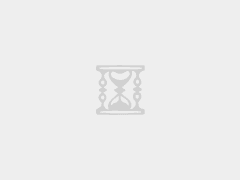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中,陈列着一套闻名遐迩的编钟,以其身铭文“惟刑鬲屈奕晋人,救戎于楚境”而得名 编钟。
编钟。
这套编钟之所以声名显赫,不但因为它保存完好、外形精美,更因为它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缘分。
长久以来,众多学者都以为是这套编钟演奏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播放的乐曲《东方红》。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这套编钟与“东方红一号”之间的机缘脉络逐渐清晰。原来这缘分背后,有着两段“不得已而为之”的往事。
从“谎言”到“一钟双音”
1957年,这组 编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震撼了考古学界。
编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震撼了考古学界。 编钟为13件钮钟。第一件钟形体较大,且钟体各部纹饰与其余12件钟略有不同;钟鼓正反两侧铸有春秋时期字体铭文,记载着春秋末年
编钟为13件钮钟。第一件钟形体较大,且钟体各部纹饰与其余12件钟略有不同;钟鼓正反两侧铸有春秋时期字体铭文,记载着春秋末年 救陆浑戎于楚国以对抗晋人之事。其余12件钟形体逐渐减小,造型纹饰基本相同,钟腔两侧置36个乳钉状枚,篆、鼓、舞部为突起变形蟠螭纹,底纹为纤细的旋涡纹、绳索纹相交织。
救陆浑戎于楚国以对抗晋人之事。其余12件钟形体逐渐减小,造型纹饰基本相同,钟腔两侧置36个乳钉状枚,篆、鼓、舞部为突起变形蟠螭纹,底纹为纤细的旋涡纹、绳索纹相交织。
当年的音乐考古调查小组根据铭文字体推断,这套编钟铸造于春秋晚期,放置于战国时期的墓中。考古学家李学勤根据出土资料从考古类型学推断,音乐史学家黄翔鹏通过先秦时期的音阶发展规律分析其音阶构成,均得出第一件钟与另外12件钟并非同套的结论。
据黄翔鹏分析,在春秋早期,统治阶级专用的宴享之乐开始以隐秘的方式使用新的六声、七声音阶。到春秋中晚期,这种新音阶被正式引入钟乐。此时,编钟的形制已转变为钮钟, 便是更加完善地反映七声音阶编钟的典型代表。
便是更加完善地反映七声音阶编钟的典型代表。
钟体上的七声音阶从被发现到确认,可谓一场传奇。
据第一批前往调查的小组所作记录,这套编钟不仅与同墓出土的竹简记载的数量一致,出土时完好得“不仅没有伤裂,连轻微的侵蚀锈片也找不到”,因而推测“它的声音可能变化不大”。
不仅如此,随墓出土的还有已经损坏的木质钟架、钟槌与铜质的穿钉,呈现出此组编钟得以悬挂、使用的方式与配件。
此前关于我国先秦乐律与音响形态的猜想大都基于对史料的发掘,而相对匮乏的先秦出土文物资料难以支持史料所陈述的那般绚繁。因此, 编钟的出土意味着我国第一次有机会可以还原先秦编钟的全貌,对于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界来说,是个令人震惊而兴奋的“空前发现”。
编钟的出土意味着我国第一次有机会可以还原先秦编钟的全貌,对于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界来说,是个令人震惊而兴奋的“空前发现”。
经过复原,调查小组对这套编钟进行了测音,并于1958年领命,录制完成当时红透大江南北的旋律《东方红》。
继承自三千年前中华先祖的编钟音色纯正而肃雅,一经传播便得到国人的喜爱。它作为中央广播电台的开播曲广泛流传,后又被各大车站、学校用来报时。
然而,这段录音资料在公开发布之初,却引发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作为调查小组成员的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在测音工作完成后,于1958年初发表《信阳出土春秋编钟的音律》一文。听过录音资料的学者旋即提出质疑。梁易撰文提出:此次发布的13个测音结果中,并未包含在实际演奏中发出的“变宫”(即唱名si)音;在反复聆听编钟版《东方红》后,认为此音“音质不如其他音响亮,音色也不如其他音优美”。
这发乎细微的提问,折射出中国学者求真求实、严谨治学的底色。
的确如同被质疑的那样,在当时,音乐考古学界对先秦编钟的认知依然停留在“一钟一音”上。在演奏录制《东方红》时,专家曾一度为“si”音的缺失而苦恼。然而在不断尝试中,专家们在第二钟的钟枚上误打误撞出这个音高,于是“不得已而为之”,将其录制进乐曲。这也就是为何录音资料中,此音显得暗淡模糊的原因。
这场不得不为之的“谎言”却开启了黄翔鹏的想象力。1977年,他作为音乐考古小组的一员,奔赴晋、陕、甘、豫四省,对考古发掘中新石器时期、商周时期的古代乐器进行测音。在调研考察中,他逐渐觉察到先秦编钟“一钟双音”的规律。
1978年,黄翔鹏撰文明确提出“一钟双音”的看法,并指出先秦编钟的正鼓音与右鼓音呈“纯律小三度”,引发学界激烈讨论。
同年,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出土,这套年代稍晚、规制更为复杂的大型编钟,钟体刻有明确铭文,标注出钟体上双音的位置,实证了黄翔鹏推论的正确性。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时代
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升空,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卫星播放的乐曲《东方红》不但“响彻太空”,更是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转播,传遍大街小巷。
据记载,在“东方红一号”上使用电子音乐的方案,在设计之初以“采用可靠性高、工作寿命长、消耗功率小、乐音悦耳嘹亮”的优势胜出。此台乐音装置于1967年研发成功,生成的电子乐段时长40秒,选取《东方红》乐曲前8个小节,重复演奏两遍,用到6个乐音。装置中6个高稳定度振荡器分别生成6个音高基频,并混以谐波来模拟合成钢片琴的音色,按照程序实时触发和衰减,将这6个乐音合成为电子音乐。
钢片琴是发明于近代的西方乐器,电子音乐艺术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相较之下,显然古老编钟的音响更符合卫星设计者们的审美,也更能契合当时中国在政治、外交上的迫切需求。然而,最终未能实现的原因是受技术条件的制约。可以想象,这个方案是妥协于技术现实的第二次“不得已而为之”。
真实的历史有着惊人的注脚能力——在如此重大的播放场景中,在寻求表达对传统文化敬意的同时,我们一方面实现了自身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无意识地牵手西方音乐“超越传统,打破束缚”的时代美学。
近现代以来,来自西方的考古学、录音技术、现代乐理与中国传统乐理、文献学等,相互交织辉映,碰撞出思考的灵光。音乐考古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经由借助西学研究方法为工具,逐渐摆脱对西学论断的依赖,绽放出自主思想的光芒。在这样的路径中,中国古代音乐的音响正在被慢慢复原,逐步找到自己独特的形态。
时间来到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发射升空,这是我国首个实施无人月面取样返回的航天器。其上搭载了以汉、英、法、意、韩等9种语言演唱录制的歌曲《星光》,以独特的浪漫向世界传递着“共赢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探测器成功返回地面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这枚珍贵的、存储了歌曲《星光》的芯片。仿佛是历史的一次回眸,欣慰地照见《东方红》里那段白手起家、卓绝奋斗的岁月。
作者简介:
钟超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研究方向中国音乐考古。
【编辑:李岩】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87头条 » 谁在太空唱响《东方红》?
 87头条
87头条 单价2万起拍凶宅底价成交 比二手房市场打75折
单价2万起拍凶宅底价成交 比二手房市场打75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