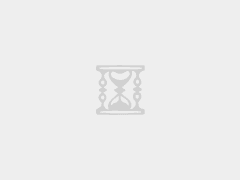编 者 按
作家和谷《寻找雷锋的蕉萍》一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发行,收录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蕉萍(姚筱舟)次子(随母亲姓)韩英(鹰)的回忆文章,真实而深刻地记述了家父的鲜为人知的往事,是对报告文学文本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在此书研讨会上,韩鹰做了《今日来黄堡》的发言,说他在六十多年的岁月里第一次来到这里,而这里是家父当年参加学习班的地方,从这里回到焦坪产生了轻生的想法,在上吊的危急时刻,是次子搭救了家父的生命。
期间,收到韩鹰的一篇题为《长兄》的手稿,由和谷一字一句辨认斟酌,更正词语和错别字,整理成文。其文笔简洁而逻辑得当,尤其是所记述的故事之感人至深,是难得的。长兄姚岩,从小被送回老家由奶奶抚养,奶奶病逝,他只得回到了父母身边,与姊妹们一起度过了艰辛而快乐的时光。长兄不幸在家父健在时病逝,此噩耗一直瞒着家父,使其到死也以为长子活着,在外为生计奔波。此等家事,由韩鹰道出,情何以堪?一首歌的背后,竟然埋藏着如此隐秘的人间故事,特殊时代的痕迹显而易见,令人沉思不已。
长 兄
一时兴起,想家和想哥,想去父母坟上看看,购票回陕。南北的气候,温差巨大有点受不了。居家无事细想,哥要是活着,也该66岁了。我们都已步入老龄,看淡了风情世事,见多了生死离别,能谈的话可能更多了。
思念是一种病,家是一种到死都难以忘却的牵绊,无论它给你带来多少苦痛、磨难,都成了老来缅怀的动力。提笔忆兄,错字、病句满篇,望见谅。毕竟是一个初中文化之人,有点蚂蚁观象看不清头尾,只觉心事诉出,无关别人怎么看,血还是热的、红的,只言片语加着归乡之泪。是的,我想家了,哥,我想你了……
长言道,长兄如父。这句话,用在大哥身上再没那么恰当。一是眼神相貌,二是性格,那么忧郁,那么无助的欲言又止的谈吐方式。虽只随母去了多年,家父也仙逝三年期满,那种样子依然常在梦中见到。
我们姊妹四人,长兄生命的最后几年间是同我走得最近的。因经历雷同,好多看法、想法,大多一样。常来坐在我的小院中,沏一杯茶,点一根烟闲聊。话题无非是父母之间为何吵架?姊妹之间、孩子们之中的一些闲事。他虽不健谈,却很愿意听我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想法和看法。有些话即便有点过分,他也只是抬起头偶尔看我一眼不做声。感觉他心中的好多话能从我口中道出,对他而言,虽痛快,却又不失是安慰和释然。我排号他是闷葫芦的性格,所以对他的到访,总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有时候拿几盒别人送的好烟,小坐片刻,我也欣然受之。
我们都是这个社会里的底层人,极其普通,好多想法、看法不谋而合。他性格懦弱,我性格秉直,相互是一种互补,自然也就谈得来。何况他终生没几个朋友,言语较少,少得连同到死亡之时口形若张,仿佛有好多读后感要说,却没有说完,就在一个雷雨交加的中午突然离去。心梗,心梗,为何心梗?我看到他若张的嘴,轻轻用手托住下巴,心中念道:大哥,有什么话,以后在梦中说吧!喃喃自语:走吧,大哥,我知道你想说啥,知道,我知道……
我同小弟给兄长洗了脸,在笛身子下塞了点棉絮,按照不系扣的穿戴好衣服。等着我妹从西安回焦坪看大哥最后一眼。
等待的时间很漫长。我和毛、小陈及大嫂、侄女商定如下:
一、因父健在,不张扬,连夜拉置火化场寄放。三天以后,火化。杜绝一切消息走漏。
二、骨灰暂放火化场,待父下世以后再择日入土为安。
三、因母亲去世还余留一部分钱,原本是给家父看病和办理后事之用,先拿出来,火化、骨灰盒、寄存、招待帮忙的费用,全部用余留之中先支,安葬大哥为重。
家中静得出奇。除了能听到大嫂的几声唏嘘声外,剩下的就是烟雾在房间中的飘渺而久久散……
我同大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1年初秋。当时是在焦坪医院。医院是用并排的蓝砖蓝瓦建造,中间是过道。左边是医生看病的办公室,右边是病房,不分什么科别,只分男女的那种。母亲因砖厂塌方,而骨盆骨折住院,住在右边第一间病房靠窗的床位。医院下方是原露天下坑马路,上方是三线建设尚未完工的铁路,中间夹着露天用铁丝围着的木材加工厂和圆木堆放场。木材厂和医院只隔条马路,进出煤坑均得在此通行。每日生活的人们和各种车辆都从此通过,这里就成了晴天是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车辙很深,路上黑乎乎的灰有一拃厚,而且坑凹不平。夹在中间的医院,早已没有当初的模样,变成灰头土脸的一排灰房子。如没有窗户,人们都不知道怎样区分。就这也是焦坪矿区早期发展时的第一医院,也是唯一的有床位的医院。
当时焦坪是由露天矿为主,架空索道尚未停运,东背塔平峒还未建成,前卫斜井还在紧锣密鼓地盖办公楼和职工宿舍。永红矿叫军工矿,是由部队人员管理开采的。整个矿区虽是脏乱差,到处是尘土飞扬,却也不失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焦坪露天是最大的,也是西北地区产量最高的。露天煤矿,有东北的电铲,电力剥荒的小机车,一段、二段、三段、机务段、办事组、行政科、后勤组、职工宿舍食堂、澡堂,一应俱全。
当时,爸就在紧挨着煤坑的采煤一段下放劳动。由于个子低,1.68米,体重近90斤,瘦小无力,而被分配做了信号工。工资虽不高,35元,28斤粮,好在还有姥爷煤坑抡大锨的56斤粮、66.34元工资帮衬着,全家生活也还过得去。穷是穷了点,只要没什么政治运动、游街、批斗、不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也算是很幸运的了。40%的粗粮,每人每月半斤大米、二两油。家中我常去排队买粮,也从购粮本上知道,我是吃16斤粮的标准了。
姥爷做好饭,看着你们仨吃完,用搪瓷缸盛了大半缸子,用纱布裹好,系了扣,交给我说:给你妈送饭去。
妈吃着饭,我贪玩,就出了医院病房在外边玩,看见爸用很短的竹扁担一头挑着个木盒,另一头是个长不长、方不方的木箱和一个小布袋。前边走着一个比我高低差不多的男孩。我当时灰头土脸的很脏,那男孩倒是白白净净,虽不胖却很清秀。穿的也很得体,深蓝色的小夹袄,学生领,下面还有两兜,额头很高,眼大有点凹,脸色有点黄,脸庞清秀冷峻像我爸。我心想,这可能就是爸回老家接回的我哥吧!太像了,尤其是那两颗有点暴凸的门牙,真的太像了。我猜想肯定是那个拉煤车给爸捎回来,在这儿下车的。
爸担回的木盆,是用木板一块一块箍成的那种,大概有十七八块。盆底也是木板合起来用胶粘好,锯成圆形,一圈是用竹条箍紧不漏水。红色的木箱很薄很轻,外面有“紫坛”两个隶书凹雕大字。
当时我很小,不知是干什么用的。长大后听爸说,是奶奶的手饰箱。奶奶过世后,给了你哥做放书的书箱。
我记得箱子里有我看不懂的几张地契,有二套《芥子园画谱》线装的蓝布面,一套是山石树人,另一套是花鸟鱼兽,合计八本。箱子下面有两个小抽斗,内外都是双铜扣,可以上锁。我感兴趣的是哥哥南方带回的连环画本,有《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东平湖的鸟声》等等十来本。这是后话。
爸担着东西进了病房,放下东西,转身拉着我哥进来说:“淑华,这是小平。”
母亲脸上流着泪说:“小安,这是恁哥,叫哥!小平,这是恁弟,叫小安”。
我傻傻地站在病床前,看着妈流着泪,脸上却露着笑容。
妈说:“还有你妹叫丽萍,最小的叫小毛,他俩都小,你姥爷在家看着哩”。
哥没有回答一句,只是一脸慒懂,站在很远处看着妈,如同妈说的是外国话。是爸说了一句话,才给妈解了围:“孩子才来,话还不太懂,过一阵子就好了。”
妈指着我俩,用很浓的苏北口语骂了声:“憨熊,两个憨熊!”
这就是我十几年未见,确切地说,是吃大米饭十几年未见的哥哥。
语言的隔阂,生活习惯不同的大哥,和我们陕西生、陕西长的姊妹仨,语言上很难沟通。因为不习惯面食,全家的大米都给了凶一人吃,换回的的是一句“米饭不好掐”。
大哥的奶奶带大的,很干净,很会整理自己的内务,书包、本子,包括小人。我常常偷拿哥的画本看,看完随手一扔,为这,我们兄弟常常打架,关系时常不好。因为在老家有奶奶宠着,在这有姥爷、爸妈护着,都上到初中我俩也没有多少话说。
等我们兄妹都大了点,父母托人给我们兄弟仨在十三排窑洞楼头,要了三小间。进门是炉子,中间窗户明亮,大哥一人住,我同小弟住靠公共厕所大门的最后一间。
天生的优越感,家里担水、劈柴、拉煤的活儿,大哥也很少伸手。仿佛和我们仨“出身有问题的狗崽子们”不是一窝的。
环境造就的性格,天生孤僻、言语寡淡,到死也没改变多少。
父亲在我们姊妹走入社会前,很少打我们几个。倒是母亲说骂,张口就来,只要我们谁做了错事,随手捞起扫把、木棍就朝身上抽打。小时候,没少挨打,当然,挨打最多的依然是我。
爸的方法是叫我下跪,一跪就是几十分钟。跪后还要写检讨,检讨一遍一遍地写,错别字一遍一遍地的改,直到他满意后,方才叫我起来吃饱。
我是我们姊妹当中唯一的叛逆者。好动爱惹事,还不服输。老师家访,邻里告状,尤其不喜欢听说教式的训戒,叛逆心理极强。大多是我惹事,父母给人家赔礼道歉,严重的还得给人家赔钱。当然,我的报酬是一顿饱打,逃学,夜里不敢回家是家常便饭。
哥哥弟弟妹妹学习都好,也比我听话许多,我在家是最不受待见。可我窑洞那一片,直至我下乡参加工作以后,人缘都很好。虎朋狗友也不少,坏是坏了点,可家中的大小活,我总是首当其冲。
小一点拾柴,大点了用架子车拉煤,买粮、喂猪、盖房拉砖拉土,偷油毡搧房,基本上都是我们那帮“坏孩子”们帮我做的。这一点,我很感谢他们。有时,爸妈还做几个菜,允许我们一块喝点小酒。
一直到我招工下井,每月能开五十多块钱,只留几块零花钱,全部交给母亲,除还账外,余下补贴家用,父母的态度才转变了好多。但和大哥还是很少说话,我记得说的最多仍是那句“掐饭了”。在统配经济逐步河开冰消时节,我们家也生活平稳,爸有有了自己的朋友群,张任田、马琳琳、梁志民、李振熙、杨西敏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家生活大致相同,没有什么攀比之处,最多的是谁家孩子穿的干净整齐一点。在涤确良出现之前,我记得爸给我妹买了件麻纺格子尼上衣,绿底橙色格,妹爱不释手,穿了很多年。直到穿着都小了,袖子短了一截还不舍得脱。男孩们大多是爸发的灰色工作服,改一改我们轮着穿。
童年是一瞬间就没影的时代。能让我受益最大的就是写检讨,感谢经常写检讨,成就我参加工作时多多少少有点沾沾自喜。因为单位领导发现我字写得不错,就叫我写宣传稿,表扬区队、班组里的好人好事,出黑板报,写写画画,完成上级宣传组交给的政治任务。
在我与工人师傅们同下井共挖进的日子里,得知他们都是富平、蒲城、三原及陕北农村招来的轮换工,文化基础很低,有的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能把自己名字写规正就不错了。三年期满,大多还是回到农村继续种田。像我们这批从农村招来的知识青年,自然就成了每个区队的新生血液而倍受器重。
这里焦坪矿是蒸蒸日上,一派欣欣向荣景象。那个区队挖进创新多少米,创了井口纪录,那个区队单班产煤量创下建井以来最高产量,进尺第一。安全生产只是口号,实际排在第二。经常可以看到井口领导叫工会举着喜报,拿着慰问品,敲锣打鼓地流窜于区队之间。慰问品都是很廉价的西瓜、肥皂、毛巾之类的东西。真正让区队长们由衷高兴的是能多拿奖金,和矿长、书记招待区队长的好烟好酒,和区队长们嗟一顿。对我们来讲,悬挂在区队学习室墙上的锦旗,就是最高荣誉了。
我们的成长,无不烙下时代发展的印迹。只要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只要你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在生产中,你就能感受到各各齐努力,人人争上游的浓厚气氛中。宣传标语、高音喇叭、慰问喜报、黑板报,耳濡目染了这种日子。整天忙碌着算工资、发工资、领劳保、发劳保,写各种表扬稿。闲暇时给工会冬日帮帮忙,打打乒乓球、羽毛球之类的文体活动,生活倒也充实自在。
生命是很脆弱的,一场常有的井下冒顶事故,夺去我下乡时农友的生命。昨天晚上上班前,我们俩在我家为生活琐事谈了很久,今天早上就听人扒出来已没了呼吸。肋骨断了七根,有两根戳进心脏,年仅二十岁。
这事对我怵动很大。静下来反思过往,自己的性格过于耿直。又不想给领导送礼,主要原因是领导班子该换届了。反复思考后,向主管领导谈了自己想法。理由是家庭出身原因,自己还年轻,想下车间学门手艺。领导听罢,说:“过几天给答复”。
这也许是我的小聪明正中领导的下怀,谁不愿在重要岗位上安排自己的人。许愿我,车、钳、鉚、电、焊随便挑,月底交手续。
那年月,国家政策已宽泛了很多,爸也基本上恢复干部名誉,工资五十五元。母亲身体不好,出不了力,在二小做保育员,给教师们香孩子,每日一块三毛六分。我从下乡到招工已满五年,政策之内带级学徒四十一元零二分。三年期满升为三级工。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国内国外一片形势大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到处一片莺歌燕舞,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跨步向一个新时代”。这都是报纸杂志说的我们每一个工人耳熟能详的话。
市场是繁荣了许多,矿上有了修表店、私人裁缝铺。轮回工人从家乡拉来自己种的西瓜、桃子、柿子,拉到矿上换几个钱,养家糊口。子女上学,收国库券换衣服的,换麻将的满街都是。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二两饭票五分钱的汤面里有肉了。
那里的我,三五好友,凑在一起,找个小饭馆,喝酒闲谝,当然只是一毛九分的宝成烟,和块把钱的小角楼和江口白酒。恒大、墨菊、秦洋特曲,柳林春是逢年过节、办事求人,才买来送人的礼品。
家里终于添置了几件家具,是我的虎朋狗友们从井下拉的原木解板做的。副食券、布票、粮票渐渐地消失了,逢年过节也可以买到附近农村人拉来的大肉,才块把钱一斤。市场的开放就是繁荣,我有自己的白衬衣、条绒猎装,和十几元一双的上海造的皮鞋。
不记得那天,爸下班回来告诉我们几个,以后的各种登记表成份一栏,应该填上“革干”两字,就是革命干部的意思。
没过几个月,爸又叫公安吉普车带走了。大约四十天左右,吉普车开到家门口,放下了我爸开走了。后来听爸讲,被带到福建沿海向我伯伯喊话去了。先去了北京国家统战部,再到福建沿海的。最后又去了江西,看了两位在武夷山劳改释放的三叔和四叔。此时,已经是1984年的夏天了。
大哥已从农村招工,爸托人给安排在平洞生产组,做地测科学井下测量。
我下车间,顺利地做了车工学徒。
弟上高中,学习尚好,老师常到家,说弟是考学的料,让家长多操心。
妹已在服务公司上了临时班,每天一元零八分。
生活的春天来了,来得如此之快,使我们这个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爸就调到局矿工报社任矿工报第四版文学编辑。家也在矿务局家属院分到一套五十六平米房子。生活就像姥爷常说的“你吃了多少苦,将来就有多少福”一样。爸妈脸上常有了笑容,我们兄弟俩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妈不太上班了,经常在她们老姊妹、老邻居之中,游东家、窜西家,为我和哥哥拉线牵媒。听爸妈言语中,妹妹在谈对象。
生活是丰富多姿多彩的,我们家和千百个矿工家庭一样,每一天都能听到喜讯。邻里家谁家的儿子招工了,谁家女子招工到了铜川。在这个四周环山的焦坪矿区居住的四万多人,仿佛都迎着阳光,抬起了头,成了国家发展的主人公。青山松柏绿了,久违的矿区一天天地变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附录:
长兄姚岩:幼年随祖居石塘,示冠伤逝返回北方,怎奈命中无甲子,奈何桥畔伴爹娘。
次子韩鹰:良心、善心、孝心,心安在何处?立家、顾家、念家、家居何方?累了、倦了、困了,一了尽了。
致胞妹:富贵卯中定,姻缘居其中。春风迎秋雨,情在天自成。二老下世未身近,岂缘奈何女儿身。尘凡无意百般庞,无悔天地于孝心。
致幼弟姚虹:何故侧卧山林间,只因美酒催人眠。放眼天下江山改,人间路辛酒杯满。行商贾,愁归酬,多少亲人白了头。仰天长啸浮云渺,得此悠然也自由。半生风雨半生寒,一杯浊酒敬流年。回首过往半生路,七分酸楚三分甜。性自顠淡情自高,生于乱世自逍遥。本是封侯耀祖客,怎奈惰性缘自消。
姑母在上:受侄儿一拜。二次归家,受姑母教诲,倍感受益之多,也让侄儿明白了许多道理,晓得了家中发生的许多事。尤其是看到你同姑父的近七十年夫妻恩爱如初,相濡以沫,实让人感动。看到你诗词歌赋的功底,及对民俗的深刻诠释,深感你这才女为什么高寿。开明,不知是世态的炎凉,还是岁月的磨难,让你已看淡了一切。岁月让你老人家已学会了管理自己心绪,看淡了儿女纷争,对事对人,已无争无望,活得是那么坦然明白,真不愧是姚家的栋梁。我父比你差之甚远,因为到死也没明白为什么活着。而您姑姑,一个人撑起了姚家所有后事。葬母,接三弟四弟回家,为他俩成家。而后失女,葬两个弟弟。这么多的烦心事,就没有听到你一句的怨言,想想都让人感动。我们姊妹当以您老为榜样,学您的坦然、淡定,不悲不怨,懂得感恩。从这一点上看,您是我们姊妹永远学习和尊重的敬佩之人。望天佑姑母,早日痊愈,再多留恋尘世几年,待有时机,吾带儿孙去拜望您。
愿早日病好,来年再与姑母相见,以叙亲情。
一切顺心如意!
侄儿 韩鹰
今日来黄堡
今日来黄堡,心中五味杂陈。童年的记忆里,家父就是在黄堡办完学习班后,才有了轻生之念。我终生难忘。今日赴邀,是平生六十几年第一次踏上承载了太多回忆和联想之地。
造化弄人,事过境迁,谁又能料想到,恰恰是这个黄堡书院之主人,为家父呕心沥血,走南闯北,查资料,观档案,在支离破碎的废纸片中,寻觅踪迹,追根溯源,用一支灵巧的绣娘之手,写成为姚家近百年变迁、发展、流离,及家父参军入朝,来陕居家立业,创作及歌曲承传的波折史书。
我心生敬畏,感恩岁月磨难,感恩风雨历程,感恩和谷先生历经数年、艰辛劳作为家父著书立传。让我们做儿女的,知晓家父的前情往事,看清了姚家一脉在近百年的风雨历程,是姚家在社会变革中的起起伏伏,如影随形的呈现。在这里,让我代我弟妹,向和谷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深深的鞠躬之谢!
先生无愧于一个合格的铜川人,一个对得起生养你的这片土地的铜川人,一个让家乡能为你自豪的铜川人,一位谦逊而祥和的古稀之人。今日得见素颜,实属幸事。愿先生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身体康健百年。
顺祝书院,为发展转型中的铜川添柴助火,广结人脉,纳百般贤良将才而用,为铜川文化之基业,为一个更加干净、绿色、欣欣向荣的铜川,搭上国之高速发展列车而发挥余热,为家、为家乡、为乡里乡亲,为铜川更美的未来,永不息笔,再呈光辉经典之作。
谢谢!
姚 鹰
来源:黄堡书院友情提示:凡黄堡书院公众号原创文章,转发者请注明来源,违者视为侵权。
文學陝軍专访鲁迅文学奖得主陈仓:作品是活出来的,是用皮肉熬出来的
【编辑】子 小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87头条 » 蕉萍次子韩鹰回忆:长兄
 87头条
87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