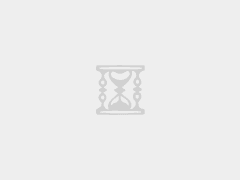“未末之乱”考
——论未指木中、朱未同字、制字本义、未末颠倒及相关问题
谭俊江
【摘 要】笔者因“末”字隶定存在明显问题,产生“未末颠倒”之疑。而此疑成立前提,在于“未指木中”。又因甲骨文“朱”“未”偶有同形引出“朱未同字”之疑,而此疑成立前提,亦在“未指木中”。笔者窃谓“制”字本即“制作”之义,而“制”字“刀加于未”则为加工“木中”即株干,这就意味着“朱未同字”,亦即“未指木中”。而把这一假定放到相关情境中验证,由“未指木中”能够顺利引出“未”的否定词义,模拟出“未”生“味”义的过程,同时也为“未”被假借为地支第八找到了根据。如果此说不谬,则“未末”就的确是被颠倒了。
【关键词】未指木中;朱未同字;未末颠倒;制字本义;否定副词;滋未;地支第八
“本”字倒置何以得不到“末”
如果用成语“本末倒置”做一个文字游戏(颠倒字形),将得到什么结果呢?
基于中国文字的表意性,“本”字倒置得到的应该是“末”字。比如把秦简 “本”:

(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下同)翻转倒置,得到的是 ,正是秦简“末”:

再把它倒置,翻转回去的还是 “本”。金文“本末”如果去掉其装饰性,也会收到同样的效果。而每一次翻转都会让人产生一种会意的快感。
这就是中国文字,这种恍然会意,就是中国文字认知过程中应有的感觉。“本”字木下有一作为指示标记的短横,意指树根之所在。“末”字木上也有一作为指示标记的短横,意指树梢之所在。而一翻转,这一短横就会随之转移至相反的位置上,成为标示相反概念的意向所指。多么巧妙,我们无法不佩服先人的智慧。
那我们就怀着对祖先的崇敬,按“本”、“末”古字笔意再做一个隶定游戏吧。
秦简“本”字:

隶定,应该在隶定后的“木”下加一短横作“本”;
秦简 “末”字:

隶定,应该在隶定後的“木”上加一短横作“未”……
且慢!有问题!
这可不是“末”字,而是我们今天普通话读作“weì”的那个字。而被我们读作“mò”的“末”字却没有出现在“本”字“翻转”的结果位置上。也就是说:
★秦简“末”字按部就班的隶定结果居然是“未”字。★
怎么回事?!
大约两千年前隶定的“末”字,短横(指示标记)没有标在木上,而是标在了木中。笔者总觉这应不是我们祖先造“末”之初衷。因为按照短横的造字功用看,将其标在木中就应表“木中”之义。在类似金文、秦简这种比较古老的“本”、“末”字形中,短横都是指示标记,那么隶定“木上”之“末”时为何要把短横标在木中呢?
再者,秦简“末”:

字忠实隶定的成果怎么成了“weì”呢?“weì”可不是“木上”之义啊。那么“weì”又该是什么样子呢?看来还不只是“末”字隶定的问题。
“未”“末”两字,是汉字教学中的难点。讲解难,记忆难。关键是说不出道理,只能记哪个横长哪个横短。单说“末”字,其字义为“树梢”。这样一个意向所指如此明确的字,其字形居然会难记!好像不太应该。这里似乎有什么原因。这两个字是不是弄颠倒了呢?
如果“mò”写作“未”,并说明其表示树梢,所以在木上加一个指示标记“短横”。那么这个字还会难记吗?据此推理,“末”是在木中加一指示标记,应该指木中。如果这个念“weì”的字确指“木中”,那么这个指木中的字还会难记吗?
可现在的问题是,笔者的这些疑问和推理都站得住脚吗?
“未末”是否被颠倒,“未”字是否指木中
“末”字隶定出问题的原因,在于其依据的不是正确表达了“末”字本义的金文“末”

或是秦简“末”

而是已经“讹变”了的小篆“末”

(说讹变是相对于原初的造字逻辑和手段),加之隶定不是按照将“末”字所本之“木”先作为主体隶定,然后再加上指示标记的程序进行的。可能的情况是,隶定者所本之逻辑乃:“木上曰末,从木从丄(丄:小篆上)”。与甲骨文之造字逻辑以及金文秦简的逻辑继承是有出入的。而由此隶定的“末”字,用本是翻转不出来的。它虽在小篆自身体系内可以自圆其说,但放在更广泛的文字发展史中看,就显出其谬误性了。站在历史的逻辑上看,它违背了造字初衷。由此而得的隶定结果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认定这一结论,也就是认定“未”字占用了“mò”的字形。而“mò”也错拥了“末”字字形。那么“末”该是谁的字形,“未”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但“未末”的关系搞不清楚,连“本末”之间的字形关系也存在问题。“本末”字义不存在问题。其本形也可依义推得。就是这个“未”字有点来历不明。关于“未”字,我们所知最多的就是它的否定词义,其次是“味”义及所谓的“木重枝叶形”。卜辞中的“未”字,仅见用于地支第八。而“未”之诸义如何产生,却未见有说得过去的解释。这让笔者对“未”字本形本义都产生诸多疑虑。加之上面看到的其隶定结果占用“末”字字形的情况。所以我们有必要做些工作,深究并探明“未”字本来面目,以便让“未”“末”两字各回其位。因为不能有理有据地把“weì”从“未”这个家里请出,“mò”就回不到自己的家。而要想请走“weì”,也得先找到它本来的家。那“mò”搬回“未”家後腾出的“房子”(末),会不会就是 “weì”的家呢?
我们把“本”“末”“未”放到一起,观察短横的位置,分别在木的下、中、上。按照逻辑应该分别指“木下”“木上”“木中”。“本”字毫无疑义。“木上末”应该是排序第三者“未”(正是“本”字倒置的结果),而不是字形上有“木中”表意的“末”。又甲骨卜辞中“未”字有短横在木中的字例。那“未”似乎有理由拥有“末”的字形。如果真是这样,本、末、未就建立起了相互关联的方位关系:“木下曰本”,“木上曰末(应为未)”,“木中曰未(应为末)”——“未”“末”字形应该互换。
天马行空地随便设想很容易,可有证据吗?
证据不足
小篆“未”写作

金文“未”作

两者都找不到“木中”的线索。甲骨文里不是有吗?这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因为甲骨文最能表现造字初衷,最有说服力和权威性。然而在《合集》几万片甲骨拓片中检视一番后,却发现“未”字作

者只是零星所见。大多数作
後期

形渐多。
“木中未”只在一期卜辞中“灵光一现”地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字例外,于二期以后,就再未出现。
这样少的例证似乎难以有力地支持“木中曰未”的设想。
不是数量少本身没有说服力,只要能证明是表文字本义,哪怕只有几个甚至一个例证也能说明问题。因为文字是记录、书写的符号,它从文字创制者那些智慧、严谨的大脑中形成并外化颁布之後,这些文字就基本上脱离了其创制者的“保护”(尤其在现代印刷术普遍使用之前)。“书法现象”和造字初衷的“不重合”是现实的存在。
所以从逻辑上讲:
在探寻文字源流时,取舍的依据应在对造字义理的探究而非在“书法现象”的多少上。
但问题就在于辨别何为造字本义,何为“书法现象”实是难事。数量太少本身就往往让人担心其存在只是一种“书法现象”。因为这些“偶尔”的字形,是否出于契刻者不经心笔误(刀误)或是偶尔的自由发挥等情况是值得怀疑的。

还被认作“朱”字,将“未”契刻作

形 ,或许是契刻者因自由发挥而将“未”刻成了“朱”,也似乎可以是一种解释。而“朱”即指“木中”。也就是说,“木中”这座“房子”里已经有“房主”了。“未”有什么理由来侵占别人的“房产”呢?何况“未”字早有明确释义,《说文解字》释未“象木重枝叶形”至今仍被广泛接受。在所有人的心目中,“未”字与“木中”毫无关系。
那么各家对“未”字形义又是如何释读的呢?
“枝叶”多有注释 “木中”曾无人征
汉许慎《说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也。凡未之属皆从未。
粱顾野王《玉篇》:未,味也。六月建也。未犹不也。未有不即有也。
宋司马光《类篇》:释未全同《说文》。
淸《康熙字典》:《说文》:未,味也。六月百果滋味已具,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之形……《释名》:未,昧也。日中则昃,向幽昧也……
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律书曰: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淮南天文训曰:未者,昧也……五行木老于未……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象木重枝叶也。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未”:此字形于小篆古文均无大异,唯卜辞则作

者多于作

……未字本谊说文每以滋味释之……然“未”乃象形字,滋味必犹其引申之义。许谓“象木重枝叶”,然于味则不相属。余谓未者

(穗)也,……由音而言未、

既同部,由字之旁从而言未、

复通用不别,是未、

古实为一字,特未用为十二辰符号之一,故遂分离耳。知未为

则知未之所以为味矣。
明义士《伯根氏旧藏甲骨文字考释》释“未”:象树木枝叶扶疏之形。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未,契文亦象木重枝叶之形。郭谓“作

者多于作

者”实则作

者亦多见或竟作

疑古文木、未同源,许说实不误。至许君以味训未,乃汉人诂字通习,实不足据耳。卜辞自有

字作

郭氏以

释未实不然也。……卜辞皆叚为支名字。後世或叚借为未,有未然之词。或有以味释未者,则与训味同为音训也。
林义光《文源》:木重枝叶非滋味之义。古未与枚同音,即枚之古文,枝干也。从木多其枝。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赞同林义光观点:其说近是……“未”字正象“木重枝叶”,枝干之意。卜辞“未”皆借作干支字。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未”:按《说文》谓未象木重枝叶形,可从。用为地支之一。
李圃《甲骨文文字学》:

前期或作

後期作

或

《说文解字》:“象木重枝叶也。”

当为“味”之初文。上古除肉食之外,植物当为先民日常必需之食物,所谓“神农尝百草”是也。“重枝叶”嫩而可食,後世饥年亦当以树叶充饥。味觉不得直象物形,故以树木之重枝叶之可食以喻味觉之“味”。
……
只有郭沫若对“未”字本义提出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观点。
综上所述,诸家观点各有倚重,不尽相同。“木重枝叶”、“枝”、“穗”各有所释,各有其由。然没有一家提到“木中”,连影子都没有。
我们好像一无所获。
探古生疑非狂妄 求真多问是笃诚
历代文字专家都没有提到“未”有“木中”之义。上面设想的问题是不是不存在呢?笔者还是有些疑问:“未”的否定词义由何而来?“未”之“味”义由何而来?郭沫若先生用“穗”与“味”找到联系,然释“未”为“穗”确显牵强。而且穗、叶古皆为食,皆有滋味。那么如其言“木重枝叶于味不相属”的话,那“知未为

”又于味怎能相属呢?李圃先生关于此问题的论述是感觉上最接近合理的观点。但由“未”到“味”的具体形成机制不明。而让笔者无法释怀的是:首先,笔者坚信用“本”翻转不出来的“末”一定是错误的(这是中国文字的表意特性、“本、末”原初字形以及其透露出来的相关造字逻辑所确定的);其次,“未”字占用了“末”字字形的事实也是明显的;再者,作为“象木重枝叶形”(形示茂盛之树)的“未”字只能给人以“有、多、好、已经、成了”之类的肯定性暗示,绝对引申不出“不、(还)没有”的否定性词义;还有,我们的祖先,甲骨文的创造者,其作品真的会这样不注重逻辑,也就是说,他们真的尚且处于浑浑噩噩,只会用描摹物象来表意的阶段吗?这一切都应该摸个水落石出。
木中同有一横 朱未是否同字
我们先不过多地受其他释字取向的影响,顺着已有的思路继续走下去。
仔细想想,如果甲骨卜辞中,满目都是“一在木中”的“未”字,这个问题怎么会留到今天。问题在这里,课题也应该在这里。甲骨文“木中未”虽然不多,但却不是没有。这就是问题!问题应该这样问:甲骨文“未”字为什么会有“一在木中”之形呢?是随意一划,还是点义之笔呢?在甲骨文中通常作为指示标记的短横“一”能是随便乱标的吗?短横毫无“象形”意味,把它标在木中如果不是用作指事,又能有何作用呢?在甲骨文“未”字诸形中哪一个才是表造字本义的呢?
……
从甲骨文资料中找到足够数量“一在木中”的“未”字,从而证明“未指木中”,当然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明了的途径和方法。但路却不一定只此一条。那么途径和方法又在哪里呢?笔者试图扩大思路,在与“未”字字形相近和由“未”作为字素的文字中寻找线索。那就先从上面提到的那个“木中房主”——“朱”字入手吧。
方述鑫等《甲骨金文字典》释“末”:“本指木下,末指木上,朱指木中。谓此为一株树木,为株字初文。”此前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释“朱”:“朱实即株之本字……赤心木一解当是朱字别义,自别义专行遂另制从木朱声之株字以代朱。非浅人类居之,一在上一在中一在下之说亦不误。”也就是说,“朱”字字形是“一在木中”,字义是“朱指木中”。而笔者对“未”的设想是“未指木中”,“一在木中”。如果“朱”与“未”同指“木中”,其甲骨文又有同形的情况。那么“朱”与“未”会是什么关系呢?用卜辞“未”

字证明“未指木中”显得数量太少,而把它仅仅当做笔误又似乎说不过去。
出现“木中未”的那个时期,甲骨文“未”字的绝大多数都是

形,说添加之“短横”是笔误于理说不过去。因为那些甲骨文“木中未”

明显是专门为那一“短横”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位置。而“一”若是在

形“未”上误加之笔,此外,表“木”之形在木上多加一对斜枝尚无大碍,而在甲骨文中具有指标意义的短横按说是不会随便乱加的。所以它们会不会是同义甚至就是同一个字呢?
甲骨文“朱”字十分罕见,卜辞中仅见于地名,且字形也与“木中未”基本相同,所以释其作“未”也似乎未尝不可。将其释作“朱”的根据是其与金文“朱”的字形延续关系。其金文作


那么尽管“一在木中”的“未”字不是多数,但毕竟存在,所以也没有理由确认它们之间就没有字形的延续关系。只是仅凭这些还得不出结论。
这里我们再引入一个与此相关的字——“制”
解释“制”义由来的过程,也是验证“未指木中”佐证“朱未同字”的过程
小篆“制”字

左边是未,右边是刀。《说文》释制:裁也。从刀从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
从许氏释未 “象木重枝叶形”出发,刀与枝叶所能形成的逻辑关系的确是“裁”。但“裁”“制”虽然并用,却非同义联合,各有所喻,互有区别,“裁”非“制”也。故其释义有些牵强。而其对“制”字词义来源“物成有滋味,可裁断”的解释,更是牵强。
日本学者白川静《常用字解》释制:

会意,“未”与刀组合之形。“未”乃枝叶茂盛之木。伸出的枝杈用刀(剪刀)剪切,进行剪定整枝,谓“制” ……
裁枝整形谓“制”,比用“物成有滋味,可裁断”释“制”符合形式逻辑。然而其释义虽然看似有些道理。但却太不符合实际。与上古先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可不是给树枝整形(园艺技术的普遍使用也不应是那个时候的事),而是制造遮风避雨的房屋和生活必须的器具。制造或制作本来就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活动,贯穿于人类发展的整个过程。“制”字本义也理应在这样的生产活动中产生并表示这种生产活动。何须到裁枝整形之类的当时都不一定存在的边缘活动中去转借呢?
上述观点必须强调。因为它表达的并非笔者意见,而是在此处被忽略了的常识:制造、制作等活动,远比修枝与先民的关系密切得多。所以制造、制作的概念(具体表现为词)肯定是伴随着人类制造、制作的社会实践而产生的,绝不可能是从别处假借的。而表达其概念的文字,也一定是对相关实践状貌与意向的表现。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而且真实地反映着人类的社会实践。在“状物示义”的过程中,先取与自身及其活动关系近密者,无近密则渐次远疏理应是先民所循途径之必由。这才是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
所以“制”的本义,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是“制造”或“制作”之义。
上古时比较普遍的制造制作,是对木材的加工,亦即《周礼·考工记》首推之“攻木”是也。而用为制作原料的木材(原木)是树木的哪部分呢?是去掉本末(根梢)的“木中”——笔者所言之“未” 。正如小篆其字——“刀加于未”。而只有当“未”作“木中”解亦即株干(朱)时,“制”字之义才能符合历史真实。所以从“制”的字形词义看,“未”字也应该指“木中”,且与“朱”同义。这样解释既符合逻辑,也符合实际。而如果将“未”解作“象木重枝叶形”,则刀加于未的“制”

就只能得出“修枝”这样似是而非的解释了。难道我们的先民无法在对木材的加工中体会总结出“制造”“制作”的概念、词语和文字,而非要以“载枝整形”来诱导出对“制造”“制作”的理解吗?以偶见释常见,以偏狭释广泛。其有违常理甚明矣。
据此笔者认为,“制”的本义是 :“状木材加工,示制作之义”。亦即木之中部即株干曰“未”。将此去掉本末之“未”(株干)用刀(工具)裁整加工,以为可用之器具谓“制”。字义来源由“刀”与“未”合,会“以刀制未”之义。说明“朱”“未”同指木中亦即“株干”。加之甲骨文“朱”“未”同形,应为一字。而“制”的字形词义即佐证了“朱未同字”。所以可以得出判断——“未指木中”。
“制”字释义不确、甲文难寻,皆因不知“朱未同字”
关于卜辞中有无甲骨文“制”字,目前尚无定论。
《甲骨文字诂林》、《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字典》、《甲骨金文字典》及《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均未录入“制”字。《说文解字新订》亦未录有甲骨文“制”字。笔者只见《甲骨文字集释》和《战国古文字典》录有其作者认为的甲骨文“制”字。也就是说,所见甲骨文中,还没有被公认为“制”的字。
这里例举几个与“制”相关的释字条目:
1,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释“制”:
…… </p>
<figure>
<p><img decoding=)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87头条 » “未末之乱”考——论未指木中、朱未同字、制字本义、未末颠倒及相关问题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87头条 » “未末之乱”考——论未指木中、朱未同字、制字本义、未末颠倒及相关问题
 87头条
87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