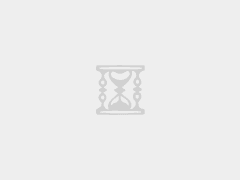我出生在赣西莲花的山野乡村,是从小伴着杜鹃的啼叫声长大的。幼时村庄被茂林修竹掩映着,清澈见底的莲江河绕村而过。两岸是数不清的白杨垂柳、灌木苇丛,那是鸟儿们栖息的乐园。当中有黄鹂、喜鹊、画眉;有斑鸠、燕子、八哥;还有就是杜鹃、麻雀、大雁……“小斑鸠,咕咕咕,我家来了个好姑姑……”“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这些儿时上小学时读过的课文, 时隔几十年后仍然十分清晰地印记在我脑海深处,时时勾起对天真烂漫童年的绵绵回忆。
许是天生就与树木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小就喜欢攀竹爬树。用两手分别抓住左右一根竹子,能一口气蹿上随风摇曳的竹尾,然后一个鹞子倒转身,让屁股在上头朝下地悬空吊挂,直惊得在底下翘首仰望的同伴们瞠目结舌。仲秋时节,经常爬上比屋栋还高的板栗树梢,去采摘别人因鞭长莫及而难以获取的板栗。尽管板栗树质脆性燥,枝干容易折断,且树大招风,人在上面就像荡秋千似的摇摆不定。但凭着我如猿猴般敏捷的身手,从未失手或遭遇过不测。至于上树掏鸟窝就更是我的拿手绝活了。家中不时驯养着从鸟窝掏来的斑鸠、画眉或八哥的幼崽,长大后能随时听从我的呼唤调遣。然而,唯有杜鹃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鸟,也是我一生中曾因冒犯啼血杜鹃而差点赔上了小命的沉痛教训。
杜鹃是学名,家乡人是从不这样称呼的,而十分亲昵地叫它“布谷”。这实际上是杜鹃的叫声,这声音我最熟悉不过了。每到农历谷雨至立夏时节,几乎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布谷、布谷”的声声叫唤。往往是晨曦微露的天色,村庄田野静悄悄的。只要一听到“布谷”的叫声,人们便纷纷趁早下地,或耕田锄草,或播种插秧,开始了一天繁忙紧张的劳作。
杜鹃的体型较小,比麻雀大而比喜鹊小。全身呈暗灰色,尾羽沿羽干两侧及内缘有白色细点。下体其余部分白色,杂有黑褐色横斑。常栖息于山野林地,喜嗜毛虫,是保护庄稼和树木的益鸟。春末夏初时,常昼夜不停地叫唤,叫得眼睛嘴巴里都能滴出血来。据《本草纲目》引唐陈藏器《本草拾遗》:“人言此鸟啼至出血乃止。” 白居易《琵琶行》:“其间旦暮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由于孩提时的一次经历,才使我亲自见证了杜鹃啼血那惊天地、泣鬼神,令人动容、催人泪下的悲壮一幕!
记得那一次,我和一帮小伙伴去河边大树上掏杜鹃鸟窝。当我爬上高枝,手刚伸向鸟巢时就惊动了杜鹃。许是一公一母的配偶吧,它们嘶哑着嗓子哀声啼叫,像利箭一样从两边向我夹攻袭击。我突然间惊得心慌意乱,一只手死死地抱住树干,另一只手拼命地驱赶扑打,生怕杜鹃啄瞎了我的眼睛。曾听大人们讲,杜鹃是极其护崽的,尤其是在产蛋孵化期,攻击性特强。为了保护其幼崽,会奋不顾身地舍命与来犯者拼死搏斗。据说邻村的麻子王大伯脸上的麻坑就是被杜鹃啄的。此时我的头颈上已被杜鹃狠狠地啄了几下,情急之中,我用手扳断了一截树枝驱打杜鹃,随后又对着上面的鸟巢乱戳乱捅一气,随即从鸟巢里滚出几个正在孵化行将破壳的鸟蛋,掉在地下摔得稀烂。此时因疼痛加上紧张恐惧,我抱树干的手不由一松,整个人便仰面朝天地从好几米高的树干上摔下来。所幸的是我掉在堤岸下的水面上,只听得“啪”地一声响,溅起一片水花。当时我的感觉是,与水面强烈的碰撞,震得心脏好像停顿了几秒钟的跳动,胸闷得喘不出气来。好在水浅,被同伴们七手八脚地拽上堤岸,庆幸的是掉在水里而不是岸上。否则,我这条小命也许就此没了。此时,但见两只杜鹃朝着鸟蛋摔碎的地方,“布谷、布谷”声声不停,撕心裂肺般地哀叫,久久不愿离开。此时,我和几位小伙伴惊讶地看到,杜鹃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颜色真的是血红血红……目睹这悲惨的一幕, 我的心灵在颤抖, 心头在滴血。从此,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伤痛和留下无尽的懊悔。
时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杜鹃好像离我们已渐行渐远了。也许是杜鹃为了躲避乡村里一代又一代顽童的捕捉袭扰;也许是因为好多年来河边的树木灌丛陆续被人砍伐而失去了栖息之所。总之,我是极少能看见杜鹃在蓝天白云下自由自在飞翔的倩影,也很少能听到杜鹃“布谷、布谷”的声声啼鸣。是啊,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正日渐受到人们有意无意地破坏却浑然不觉。在此, 我不禁要以我儿时的沉痛教训向人们敲响警钟,向杜鹃深深地忏悔并真情地呼唤: 归来吧, 杜鹃!
审阅:刘海东
简评:追忆过去,唤醒现在,值得深思!
终审:严景新
作者:贺树生,男,1953年7月生,江西省莲花县人。号玉壶山散人,别署琴鹤楼,书室耕砚斋。大学文化,中共党员。
编辑:卜一
本头条每日刊发作品优选纸刊《中国乡村》杂志,凡上刊者免费包邮赠送样刊
投稿必须原创首发,投稿邮箱:zxmtth@126.com
声明:本文为中乡美原创作品,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87头条
87头条 杜鹃潇洒了,却苦了养父母,辛苦投喂的雏鸟竟然不是自己的崽
杜鹃潇洒了,却苦了养父母,辛苦投喂的雏鸟竟然不是自己的崽 边境小城阿尔山开启“花式”旅游季
边境小城阿尔山开启“花式”旅游季 鄂伦春达尔滨兴安杜鹃赏花季启动
鄂伦春达尔滨兴安杜鹃赏花季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