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关于熊孩子问题的讨论经常成为热点话题。一般来说,人们批评的对象实际上是对孩子行为负有管理责任的家长。问题的根源在于家长的教养方式,…
关于“熊孩子”问题的讨论经常成为热点话题。一般来说,人们批评的对象实际上是对孩子行为负有管理责任的家长。问题的根源在于家长的教养方式,这已成为公众舆论中的共识。
然而,当对“熊孩子”发表谴责的声音变成了固定的舆论模式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网民对“熊孩子”的厌恶背后是否存在着对儿童的仇视、恐惧和厌恶的倾向。最近,作家苏小懒在微博上记录了一些家长带孩子乘火车遭受苛待的情况,因为有乘客对孩子的嘈杂行为提出质疑,孩子被乘务员“请”到餐车或车厢连接处。
很快,苏小懒的微博成为了家长们的“吐槽会议”。许多家长反映,仅仅因为孩子有些哭闹,他们就会受到乘务员的“照顾”。即使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对待,他们也承受着不可忽视的心理压力,在周围的沉默和凝视面前,似乎带孩子出行就成了给别人带来不便的“原罪”。
婴幼儿的哭闹是很难避免的,在很多情况下,婴幼儿的吵闹声并不是因为家长的教育不当或照顾不周,而是天性使然。要求婴幼儿在公共场合不闹不哭,等于要求孩子克制本能。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将因孩子吵闹引起的不适感完全归结于家长的失责,或许对养育子女的家长来说并不公平。

“厌童症”是如何产生的?评论者沈彬在他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个解释视角:“在‘秩序’‘公德’的外衣之下,却包裹着对儿童的戾气、对生育的厌恶,却被当作了爽文来吸引流量。”在作者看来,“熊孩子新闻”已经成为“新黄色新闻”中的关注焦点,通过放大舆论场的撕裂和冲突,制造了一种“仇童的狂欢”。
不可否认,身处以流量至上为特点的舆论空间,一些网民形成或巩固了极端的思维方式。在网络上,盛行“拉踩”“引战”,这既容易导致具体事件中的网络暴力,也使许多人的思维变得刻板和固执。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人们认为:孩子闹腾,是家长的错;家长辩解,是不负责任。
然而,仅仅因为一些自媒体的渲染和炒作,就能让公众对孩子的看法从“小天使”变成“小恶魔”吗?答案显然不是单一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社会情绪。
不久前,科普作者河森堡认为:“养育孩子是一个超长期的投资,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个只关注当下的人,自己不会选择养育孩子,也难以容忍别人的孩子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抚养孩子、教育孩子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个成本既包括家庭成本,也包括创造有利于友善生育和抚养环境的社会成本。当然,大部分社会成本已通过公民纳税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方式得到支付,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不生育、不抚养孩子的社会成员可以完全摆脱对下一代成长的支持责任。
例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为孕妇和孩子让座是乘客的义务;在学校和幼儿园附近,经营者依法不得开展特定的经营项目;载有未成年学生的校车在公共道路上临时停车时,后方车辆应该耐心等待……对婴幼儿在公共空间中吵闹的适度容忍也是上述社会成本的一种体现。
此外,这种容忍并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毫无底线的。例如,在图书馆、剧院、音乐厅等公共文化场所,许多都设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开放区域,或者拒绝易造成噪音的未成年人入内,这是社会规则为了避免儿童的行为超出公共利益所能容忍的范围而作出的必要限制——如果无法防止孩子突然哭闹打断一场音乐会演出,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孩子进入。
事实上,所谓“厌童症”的矛盾更多地发生在“无奈”的情况下。在社会流动和迁徙日益常态化的今天,父母带孩子乘坐高铁、飞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高铁一直以来倡导的宁静氛围似乎与孩子的特性不相容,这种矛盾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才会加剧和放大。
就像《新周刊》一篇名为《“厌童症”这顶帽子,年轻人不认》的文章所说:“一味地将传统观念移植到年轻人身上,指责他们自私,并将不结婚、不生育的困境与‘讨厌孩子’联系起来,只会增加敌意和愤怒,掩盖问题的本质——在经历了短短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城市似乎难以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因此出现了空间互相竞争的情况。”
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并不新鲜但确实切中要害的解决方案:“建立儿童友好和母婴友好的社会空间,这不仅仅依赖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自我道德约束,还需要一个包容和便利的养育环境。”
一个对孩子更友好的社会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支持和容忍,也需要切实的投入。具体到乘坐高铁的“熊孩子”问题,最近关于设立“儿童车厢”或“母婴车厢”的提议再次出现。这些建议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想象,而是瑞士、芬兰等发达国家的实际经验。这些“儿童车厢”不仅提供了专门为带孩子的家庭提供服务的乘坐空间,还设有儿童游乐区和婴儿尿布台等人性化设施。
比起“禁止孩童入内”,更文明的做法是探索一种“鼓励孩童释放天性”的空间,从而让不同需求的社会群体能够和谐相处。从这个角度看,许多人所谓的“厌童症”不是针对无辜孩子的,而是对没有充分实现儿童友好社会环境的厌烦。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87头条 » 探究“厌童症”背后的共性社会情绪
 87头条
87头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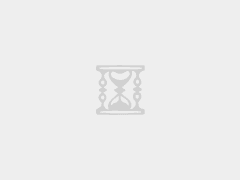
 _幼儿园教育要回归本质,新政策让家长和孩子都放心
_幼儿园教育要回归本质,新政策让家长和孩子都放心 7岁男孩偷拿钱买萝卜刀被送派出所怎样教育孩子
7岁男孩偷拿钱买萝卜刀被送派出所怎样教育孩子 7岁男孩偷带啤酒去学校同学齐喝醉家长打断衣架
7岁男孩偷带啤酒去学校同学齐喝醉家长打断衣架